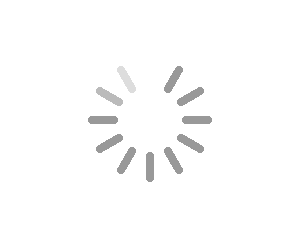马尾船政学堂是近代中国翻译家的摇篮,严复与林纾缔造了中国近代翻译传统,福建是中国思想文化现代性率先萌生之地,这已是学界共识。9月20日,福建社会科学院、福建师范大学、省文联邀请国内众多名家齐聚榕城,参加近代福建翻译与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暨闽派翻译高层论坛。
严复说“译事三难信达雅”。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李景端认为,这是一个值得传承的文化遗产,当今译界乱象太多,需要有一面旗帜来振奋人心,复兴闽派翻译,应该把“信达雅”当作一种精神来弘扬。
闽人书写近代中国翻译史
上世纪80年代的“文青”,开口便是“魔幻现实主义”,足见这一拉美文学流派人气之盛。其中的一位推手林一安,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。上世纪50年代上大学时,他原想读航海专业,却被安排去学西班牙语,闹了一阵子情绪。他说:“后来看到林纾的翻译,我愿意了。”
“尽管林纾的翻译有很多错漏,但文笔实在太好了。”林一安说,林纾、严复两位大师那种执着的翻译性格,恰恰是今天我们所缺欠的。
从与孟德斯鸠多次面谈的莆田人黄加略算起,有据可查、享誉文坛的闽籍翻译家有上百人之多,在学术、文学翻译上都有很高的成就。严复、林纾、陈季同、辜鸿铭、王寿昌、许地山、林语堂、郑振铎、冰心、林同济……一部近代以来的福建翻译史几乎就是一部中国翻译史。
福建自古以来就有以“海上丝绸之路”为基本途径的对外商贸和文化交流。可以想象,如果没有翻译的存在,这些交流活动是很难进行的。林本椿等学者认为,近代福建翻译与晚清政局变化关系紧密,体现出经世致用的精神指向,在思想文化上彰显出锐气和开放性。
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马尾船政学堂,“授课基本上用外语”的办学特色,即便是当代的一般大学也难以望其项背。振兴闽派翻译,根基在哪里?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刘传标说,首先应是教育这个主题。
1877年,马尾船政学堂第一批留欧学生35人先后赴英、法学习,严复是其中的一员。到了晚年,他在一封信中引用西人名言“革命风潮起时,人人爱走直线,当者立靡”,对梁启超“其直如矢”的思维方式表示怀疑。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认为,这种对话对今天来说是意义非常重大的。上世纪前期的中国,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怎么革命,但现在看来,我们还有其他一些思想资源需要发掘。在社会安定的前提下如何继续深化转型,这种渐进的思想就显得特别重要。
作为翻译家的严复,实际上也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转型。重温《群己权界论》等译作,陆建德深感严复在很多方面是有先见之明的。
两脚踏东西文化的大师
美国人葛浩文因是莫言作品的英文译者而成为热议人物,被不少人视为“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”。不以为然者也有。有人就戏说:莫言作品获得的不应是诺贝尔文学奖,而应是诺贝尔翻译文学奖。也有人反驳:还别说葛浩文,恐怕连他这样的翻译家都后继无人了。
有次聊到“对中国有一定了解的年轻翻译很难找”,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部副主任李洱给葛浩文出了主意:你只问三个字,就可以马上断定他是否适合。哪三个字?“吃豆腐”。葛浩文听了哈哈大笑,当场把翻译家都叫过来,结果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是啥意思。
会上,李洱又举了一个反例:在中国语境里的博尔赫斯,是一个大打折扣的博尔赫斯,因为中文世界的读者不知道这个文化背景——博尔赫斯精准、简洁的语言,是对浮夸、冗长的西班牙语风的有力校正。
杨宪益和夫人戴乃迭合作的《红楼梦》译本,在剑桥大学图书馆没人借。大卫·霍克斯的译本尽管失去了很多中国元素,却在英国的机场也可以买到……几位学者道出所见,让“传播的有效性”成为论坛的焦点话题。
翻译是背叛还是再创造?老生常谈经“把原文打碎后重新组合”一番新论的转码,被重新摆上台面,还派生出更多争议:严复的翻译实践是否达到了自己的翻译标准?林纾是不是一个翻译家?厦门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杨士焯回答倒也干脆:翻译不是万能的,目的只是达到一个沟通的作用,每一个译者都只能尽可能地去贴近原文。
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贺昌盛,曾问藤井省三为什么选择翻译莫言的《酒国》,回答是:“莫言的想象力对日本读者是一种冲击。翻译过来后,书卖得还不错。”在文化推介中能找到结合点,贺昌盛认为林语堂也是如此,他除了翻译之外,还有严格的选择、消化、解读的过程。
林语堂“两脚踏东西文化”,曾被西方时论誉为除孔夫子之外,另一位最广为西方人认识的中国文人。贺昌盛说,在“推广出去,接纳进来”的翻译过程中,要从林语堂的做法中承接经验。
靠什么支撑互联网时代的翻译
“成就傅雷这样的大家要花多少本钱?(上海)南汇400亩田。”“上世纪50年代翻译一部《青年近卫军》,能在北京买一座四合院。”两件事为老一辈翻译家津津乐道。
靠什么来支撑互联网时代的翻译?“有深厚的双语基础和认真负责的态度是必需的。”文敏是《浙江日报》记者,译过库切、保罗·奥斯特等名家名作,她认为那些技术性问题总是能得到解决的。
与上图书馆、查词典等传统方式不同,网络提升了翻译的速度。文敏说,互联网上有各种词典,包括俚语这类的低俗语言。她常上一家翻译网站,只要一提问题,就会冒出世界各地的译者帮忙,不像当年傅雷要靠与国外朋友通信来解疑。
文敏曾参加美国一家翻译公司主持的团队合作项目,世界各国的翻译都有。在交流中,她发现美国翻译对互联网技术非常熟悉,她一度把对方误认为程序员。这样的训练有很多好处。文敏现在有了个人的微信公众号,技术操作上没有问题。
真正让文敏感到揪心的是“文学面临危机”,文学翻译界稿酬过低是一个普遍的认识。
谷歌在线翻译,提供超过500种语言之间的双向转换服务。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好事,能让不懂外语的大众,不必再像林纾那样依靠合译来了解域外风景。
“作为真正文学的语言,思想理论的语言,所具备的丰富的复杂性,是翻译机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以生成的。”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韩少功认为,一字多译,这种表达方法的变化无穷,是翻译机望尘莫及的。
韩少功也看电视节目《非诚勿扰》,发现凡是说自己是“文青”的,一般被“灭灯”最多,这类人的确有些“讲话不着调,行为古怪”,他由此感叹:我们的文学为什么培养出这么一批奇葩?外国文学现在在中国最好卖的,可能是《哈利·波特》吧?对于思想文化的真正热情,何时才能在我们的社会重新激发?
作为《爸爸爸》《马桥词典》的作者,也是米兰·昆德拉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的译者,韩少功还是相信:当生活、历史逼迫我们寻找答案,而很多问题没法得到解答时,我们需要向文学求教,需要向思想理论求教。
1997年3月,黎巴嫩驻华大使在颁发骑士级国家雪松勋章时说:“冰心女士在年轻时,就敏锐地听到黎巴嫩的思想家、作家纪伯伦的哲理和诗的呼唤。”
译者毕竟不是机器。在本次论坛的会场上,冰心的女儿、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吴青站着,举起“爱”“人”大字牌,想说明母亲生前的翻译,充满了对不同文化的同情、理解。
马尾船政学堂是近代中国翻译家的摇篮,严复与林纾缔造了中国近代翻译传统,福建是中国思想文化现代性率先萌生之地,这已是学界共识。9月20日,福建社会科学院、福建师范大学、省文联邀请国内众多名家齐聚榕城,参加近代福建翻译与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暨闽派翻译高层论坛。
严复说“译事三难信达雅”。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李景端认为,这是一个值得传承的文化遗产,当今译界乱象太多,需要有一面旗帜来振奋人心,复兴闽派翻译,应该把“信达雅”当作一种精神来弘扬。
闽人书写近代中国翻译史
上世纪80年代的“文青”,开口便是“魔幻现实主义”,足见这一拉美文学流派人气之盛。其中的一位推手林一安,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。上世纪50年代上大学时,他原想读航海专业,却被安排去学西班牙语,闹了一阵子情绪。他说:“后来看到林纾的翻译,我愿意了。”
“尽管林纾的翻译有很多错漏,但文笔实在太好了。”林一安说,林纾、严复两位大师那种执着的翻译性格,恰恰是今天我们所缺欠的。
从与孟德斯鸠多次面谈的莆田人黄加略算起,有据可查、享誉文坛的闽籍翻译家有上百人之多,在学术、文学翻译上都有很高的成就。严复、林纾、陈季同、辜鸿铭、王寿昌、许地山、林语堂、郑振铎、冰心、林同济……一部近代以来的福建翻译史几乎就是一部中国翻译史。
福建自古以来就有以“海上丝绸之路”为基本途径的对外商贸和文化交流。可以想象,如果没有翻译的存在,这些交流活动是很难进行的。林本椿等学者认为,近代福建翻译与晚清政局变化关系紧密,体现出经世致用的精神指向,在思想文化上彰显出锐气和开放性。
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马尾船政学堂,“授课基本上用外语”的办学特色,即便是当代的一般大学也难以望其项背。振兴闽派翻译,根基在哪里?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刘传标说,首先应是教育这个主题。
1877年,马尾船政学堂第一批留欧学生35人先后赴英、法学习,严复是其中的一员。到了晚年,他在一封信中引用西人名言“革命风潮起时,人人爱走直线,当者立靡”,对梁启超“其直如矢”的思维方式表示怀疑。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认为,这种对话对今天来说是意义非常重大的。上世纪前期的中国,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怎么革命,但现在看来,我们还有其他一些思想资源需要发掘。在社会安定的前提下如何继续深化转型,这种渐进的思想就显得特别重要。
作为翻译家的严复,实际上也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转型。重温《群己权界论》等译作,陆建德深感严复在很多方面是有先见之明的。
两脚踏东西文化的大师
美国人葛浩文因是莫言作品的英文译者而成为热议人物,被不少人视为“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”。不以为然者也有。有人就戏说:莫言作品获得的不应是诺贝尔文学奖,而应是诺贝尔翻译文学奖。也有人反驳:还别说葛浩文,恐怕连他这样的翻译家都后继无人了。
有次聊到“对中国有一定了解的年轻翻译很难找”,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部副主任李洱给葛浩文出了主意:你只问三个字,就可以马上断定他是否适合。哪三个字?“吃豆腐”。葛浩文听了哈哈大笑,当场把翻译家都叫过来,结果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是啥意思。
会上,李洱又举了一个反例:在中国语境里的博尔赫斯,是一个大打折扣的博尔赫斯,因为中文世界的读者不知道这个文化背景——博尔赫斯精准、简洁的语言,是对浮夸、冗长的西班牙语风的有力校正。
杨宪益和夫人戴乃迭合作的《红楼梦》译本,在剑桥大学图书馆没人借。大卫·霍克斯的译本尽管失去了很多中国元素,却在英国的机场也可以买到……几位学者道出所见,让“传播的有效性”成为论坛的焦点话题。
翻译是背叛还是再创造?老生常谈经“把原文打碎后重新组合”一番新论的转码,被重新摆上台面,还派生出更多争议:严复的翻译实践是否达到了自己的翻译标准?林纾是不是一个翻译家?厦门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杨士焯回答倒也干脆:翻译不是万能的,目的只是达到一个沟通的作用,每一个译者都只能尽可能地去贴近原文。
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贺昌盛,曾问藤井省三为什么选择翻译莫言的《酒国》,回答是:“莫言的想象力对日本读者是一种冲击。翻译过来后,书卖得还不错。”在文化推介中能找到结合点,贺昌盛认为林语堂也是如此,他除了翻译之外,还有严格的选择、消化、解读的过程。
林语堂“两脚踏东西文化”,曾被西方时论誉为除孔夫子之外,另一位最广为西方人认识的中国文人。贺昌盛说,在“推广出去,接纳进来”的翻译过程中,要从林语堂的做法中承接经验。
靠什么支撑互联网时代的翻译
“成就傅雷这样的大家要花多少本钱?(上海)南汇400亩田。”“上世纪50年代翻译一部《青年近卫军》,能在北京买一座四合院。”两件事为老一辈翻译家津津乐道。
靠什么来支撑互联网时代的翻译?“有深厚的双语基础和认真负责的态度是必需的。”文敏是《浙江日报》记者,译过库切、保罗·奥斯特等名家名作,她认为那些技术性问题总是能得到解决的。
与上图书馆、查词典等传统方式不同,网络提升了翻译的速度。文敏说,互联网上有各种词典,包括俚语这类的低俗语言。她常上一家翻译网站,只要一提问题,就会冒出世界各地的译者帮忙,不像当年傅雷要靠与国外朋友通信来解疑。
文敏曾参加美国一家翻译公司主持的团队合作项目,世界各国的翻译都有。在交流中,她发现美国翻译对互联网技术非常熟悉,她一度把对方误认为程序员。这样的训练有很多好处。文敏现在有了个人的微信公众号,技术操作上没有问题。
真正让文敏感到揪心的是“文学面临危机”,文学翻译界稿酬过低是一个普遍的认识。
谷歌在线翻译,提供超过500种语言之间的双向转换服务。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好事,能让不懂外语的大众,不必再像林纾那样依靠合译来了解域外风景。
“作为真正文学的语言,思想理论的语言,所具备的丰富的复杂性,是翻译机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以生成的。”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韩少功认为,一字多译,这种表达方法的变化无穷,是翻译机望尘莫及的。
韩少功也看电视节目《非诚勿扰》,发现凡是说自己是“文青”的,一般被“灭灯”最多,这类人的确有些“讲话不着调,行为古怪”,他由此感叹:我们的文学为什么培养出这么一批奇葩?外国文学现在在中国最好卖的,可能是《哈利·波特》吧?对于思想文化的真正热情,何时才能在我们的社会重新激发?
作为《爸爸爸》《马桥词典》的作者,也是米兰·昆德拉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的译者,韩少功还是相信:当生活、历史逼迫我们寻找答案,而很多问题没法得到解答时,我们需要向文学求教,需要向思想理论求教。
1997年3月,黎巴嫩驻华大使在颁发骑士级国家雪松勋章时说:“冰心女士在年轻时,就敏锐地听到黎巴嫩的思想家、作家纪伯伦的哲理和诗的呼唤。”
译者毕竟不是机器。在本次论坛的会场上,冰心的女儿、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吴青站着,举起“爱”“人”大字牌,想说明母亲生前的翻译,充满了对不同文化的同情、理解。